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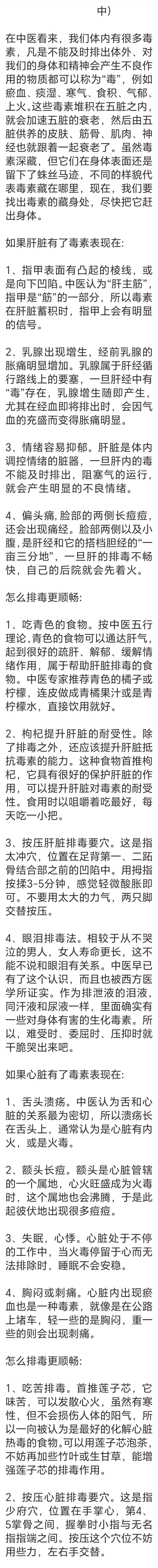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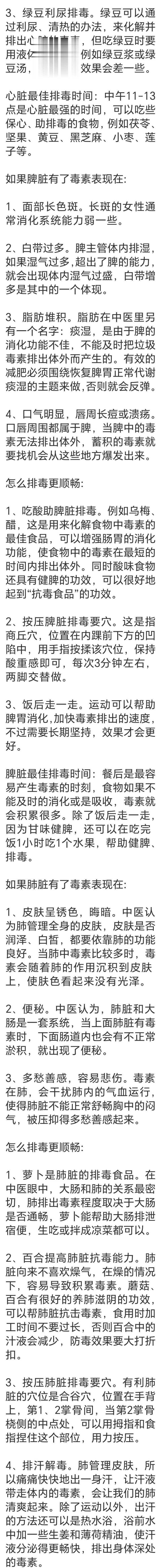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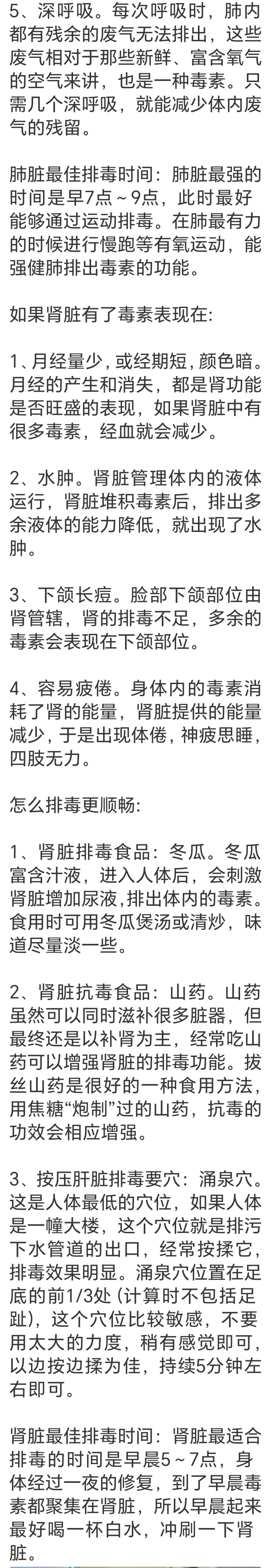
《那盏灯,那条路》
小区门口的梧桐树下,陈医生和当语文老师的妻子又为儿子的教育争执起来。这是无数个黄昏里相似的场景。
“你能不能别总逼着他背古诗了?”陈医生指着刚被训哭的儿子,“他才三年级,手指都被铅笔磨出茧了!”
李老师攥着《古文观止》:“王阿姨的孙女都能背《滕王阁序》了,现在不抓紧,以后怎么办?”
我作为邻居,默默收起晾晒的衣物。这样的对话,每月都要听见几次。
转折发生在校运会。孩子参加八百米,在最后半圈摔倒。李老师急着要冲过去,陈医生却拉住她:“让他自己完赛。”
我们看到孩子踉跄着爬起,一瘸一拐走向终点。最后一个越过终点线时,全场都在鼓掌。那一刻,孩子脸上的光芒,比考第一时还要亮。
当晚,陈医生在儿科值班,接诊了一个吞下纽扣的男孩。孩子母亲哭得几乎晕厥:“都是我不好,要是一直看着他就好了...”
这句话让陈医生怔住了。他想起白天赛场上儿子独自站起来的身影,想起妻子焦虑的眉眼。下班后,他在值班本上写下:“我们到底是怕孩子受伤,还是怕自己后悔?”
周末家庭会议,陈医生第一次没有争论。他拿出《庄子》:“子非鱼,安知鱼之乐?我们总说为他好,可曾问过他想成为什么样的鱼?”
李老师沉默地翻着相册——儿子三岁用积木搭城堡,五岁在沙滩挖渠道。那些没有被“规划”的时光里,他的眼睛总是亮晶晶的。
改变悄然发生。李老师不再执着于满分,开始欣赏儿子笔下天马行空的作文;陈医生则教会孩子包扎伤口,告诉他:“疼不可怕,可怕的是不敢再跑。”
今年儿童节,老师布置作文《我的家》。孩子写道:“妈妈是路灯,照亮很多路;爸爸是港湾,船累了可以停靠。但我知道,最终我要自己开船。”
昨夜大雨,我看见陈医生家门口多了一行粉笔字,像是孩子的笔迹:“谢谢你们,让我学着自己打伞。”
此刻,李老师正坐在窗前批改作业,台灯温暖。窗台上新添了一盆仙人掌——那是孩子用零花钱买的,他说:“仙人掌不用天天浇水,也能自己开花。”
也许,最好的教育就是这样:不是打造温室的围墙,而是让他知道,无论外面的风雨多大,家里总有一盏灯,永远为归航的人亮着。

